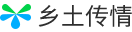编者按///
费孝通在他的著作《社会学讲义》中给出了对“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而社会学家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深入人群,通过接触个体,来理解他人与群体。
米切尔·邓奈尔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人行道王国》曾荣获社会学界最高奖项赖特·米尔斯奖,是社会学和民族志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
《人行道王国》关注的是一群在街头讨生活的摊贩。虽然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但其中街头摊贩身处的境地——被认为是混乱之源的境地——在当今许多城市管理的政策偏向中仍可见一斑。
米切尔·邓奈尔在纽约人行道上
以《人行道王国》为支点,四开和米切尔·邓奈尔深入探讨了社会学家的工作,对话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些专业知识的讨论,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感受米切尔·邓奈尔对于自身工作的坦诚与思辨。而贯穿其工作始终的主线,即“人如何为自己身处的世界赋予意义”更是每一位城市中的居住者、管理者和建设者,都应当且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社会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田野调查方法,也正在被很多其他领域借用,成为一种有效地认知世界和提供决策依据的工作方法。
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中
米切尔·邓奈尔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者,米切尔·邓奈尔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进行观察并获取信息。至今他出版过两本民族志,分别是 1992 年的《斯利姆的桌子》和1999年的《人行道王国》。前者是他的博士论文,后者是他执教后历时5年写出的作品,二者都获得了社会学界的重要奖项,在大众媒体中也广受好评。
《人行道王国》封面
日常生活中的米切尔和获奖无数的他,在我们眼里时常是分裂的。英国社会学家赖斯·贝克曾在2006年的专访中这样描述米切尔——“当我们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时,米切尔展现了和什么人都能聊的卓越能力。他能用魅力、幽默感、毫不自矜的态度和一种令人着迷的笨拙,让陌生人放松警戒。”
而在博士一年级期间,我们只感受到了米切尔的“笨拙”,因为他对网络教学平台的不熟悉造成了不少鸡飞狗跳的混乱。直到完成这篇采访的最终编辑,我们才大概理解了米切尔“令人着迷”的部分。
《人行道王国》出版的20多年后,邓奈尔作为书贩回到了纽约市的人行道
四开×米切尔·邓奈尔
Q四开这是一个面向中国读者的采访,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从《人行道王国》这本书的诞生背景开始。你的民族志研究是在回应怎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A米切尔·邓奈尔 我很高兴我们的采访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很多时候,读者倾向于在不了解写作背景的情况下阅读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民族志,将它们视作一种凌驾于时间之上的作品,以至于忘记了一本书从出版到被公众评阅,都受制于特定的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一手研究者,所有民族志学者都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书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写成的。
由于疫情期间的出行限制,邓奈尔希望通过和海外华人交流的方式,间接地向中国读者们问好
《人行道王国》这本书写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的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的街头上出现了大量无家可归者,穷人用几近侵略的方式和走在街上的中产阶级、工薪阶级产生交际。这些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互动,以及当时上升的犯罪率,最后让鲁道夫·朱利安尼成功当选并连任了纽约市长。而他最早得到选民的支持其实是基于他对纽约市无家可归者的镇压,尤其是他对一个社会学理论的实际使用。这个理论就是著名的“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通常是指小的、物理环境上的失序,将招来更严重的、引起社会失序的行为。如果建筑物上的窗户被打破并且没有得到修复,第一个看到的人会涂鸦,而下一个人可能会非法闯入。朱利安尼将这个来自社会心理学的想法运用到了人的身上——失序的征兆不再是物理环境上的特质,而是出现在公共区域的特定的人。
不在人行道上的邓奈尔通常得戴上“普林斯顿社会学系主任”的帽子——饭局可少不了
Q四开为什么民族志是适用于这一背景的研究方法?
A米切尔·邓奈尔 首先,让我们谈谈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研究。这种方法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参与、观察被研究者的生活来获取信息。实际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中是民族志的核心,你必须真正地成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对研究问题有用?因为是人类为自己身处的世界赋予了意义。他们看到世界、解释世界、理解世界,并用他们的理解对世界采取行动。我们通常将这个过程称为“对情景的定义”。
我当时对纽约市政府将人作为失序的征兆的第一反应就是:人不是墙壁或者窗户,人有思考能力,人会定义情景然后采取行动。我们不能走到一扇破窗户前询问它说:“你怎么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但对于人类,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消磨时间,了解他们作为人的真实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判断这些在外界看来“失序”的东西美国奈尔大学博士,是不是真的“失序”,去思考这些“失序”是否有着别的什么功能,身处其中的人们又赋予了这些被当作“失序”的行为什么意义。
疫情之后,邓奈尔经常会在自己的厨房里工作
Q四开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你是怎样进入到《人行道王国》中那些街头书贩的日常生活的呢?
A米切尔·邓奈尔 民族志这种方法受益于我们在被研究者的生活中找到一个角色。而我最开始找到的角色是这些书贩的助理。最初的几个月,我只是单纯地协助书贩把桌子拿出来,把书摆好,再在收摊时把书和桌子收回去。时间一久,这些书贩开始允许我拥有自己的桌子,并且还会在我的桌子上摆放他们的货物。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会始终和我的研究对象保持诚恳的关系,其原则是:我是我,你是你,我永远无法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不会改变日常着装,就像此刻我穿着一件粗花呢西装外套,如果现在要去做田野调查,那我就会穿着这件衣服去。民族志的目的不是变成你的研究对象,而是努力去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对于书贩,我就直直地走向他们,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我对你的摊位很感兴趣,可不可以让我观察。”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社会学家是什么,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最了解我的人,甚至比我的任何同事都了解我。我时常邀请他们和我一起授课,而这也得益于我的关系原则,他们不会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
作为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聘请新教授。过去几年里,邓奈尔为普林斯顿社会学系带来了马修·德斯蒙德 (左二)、帕特里克·沙奇(左三)、和西莫斯·可汗(右一)三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杰拉德·托拉斯-埃斯皮诺萨(右二)是沙奇的学生
努力去做研究对象在做的事情
民族志作为一个从20世纪初就兴起的研究方法,直到今日依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并且通常用于研究不被主流社会所“看见”的弱势群体。然而这种需要深入被研究者日常生活的工作方式,也给每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人造成了心魔:不愁吃穿的社会学家从天而降进入弱势群体的生活,在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后再迤迤然地离开。这种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让不少人都选择了伪装。社会学家佛瑞斯特·斯图尔特在调查洛杉矶的贫民窟时,就特意褪去了笔挺的西裤,换上了松垮的街头休闲裤。
邓奈尔正在和华莱士·布斯特开会。布斯特是普林斯顿宗教与非裔美国人研究的教授,他同时也是性别与性研究的主任。他们正在商讨聘请一个双聘教授的可能性
然而对于米切尔来说,伪装才是最大的轻视。无视困扰大多数人的心魔,米切尔穿着考究的粗花呢西装,径直走到纽约街头居无定所的二手书贩面前表达自己的意图。这种乍看迟钝且令人皱眉的行为,却正是米切尔“令人着迷”的地方。绝对的诚实让米切尔和这些书贩维系了一生的友情。他邀请书贩们到大学课堂进行有偿授课,并在每一年忠实地与他们分享版税——这在民族志研究中至今都是独一无二的。
2021年12月18日,邓奈尔前往纽约市向书贩们分发今年的版税收入
在研究伦理委员会制度盛行的当下,想要像米切尔一样不对研究对象匿名是非常困难的,但米切尔的工作方法对于想要进行民族志研究的人来说仍是一种鼓舞:扔掉心魔、保持诚实的我们可以与研究对象建立超越研究的真诚关系,虽然这将是一种一生之盟。
邓奈尔坦言自己正在尝试“戒掉”居家办公,因为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坐镇”也是必要的,万一学生和同事需要找他。谢宇教授在拍摄期间就正好造访了邓奈尔的办公室, 邓奈尔经常仰仗他的睿智与见解
四开×米切尔·邓奈尔
Q四开你为你的研究对象做的事情——不,应该说你和你的研究对象一起做的事情,不是所有民族志都可以达成的。你愿意和中国读者分享更多的细节吗?
A米切尔·邓奈尔 民族志研究者每天都需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田野笔记,而在将田野笔记变成一篇完整的研究报告时,你必须解释:你是如何进入这个场景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的?你的存在,即物理、社会、情感意义的方方面面,怎样影响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这些影响怎样反过来决定了你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如果你不能在写作里就这些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将非常不自在。
另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是:你到底要如何“离开”?你会保证常联系,还是就此人间蒸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各种各样“离开”的经历。《斯利姆的桌子》是我的博士论文美国奈尔大学博士,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在人行道上书写民族志,里面讲述了一群定期在芝加哥南部某个廉价餐厅碰头闲聊的黑人居民。这本书出版后的很多年内,我都会定期回去拜访那家餐厅。不过在过去的10年里,因为我成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的父亲,所以很难再随意地旅行。《人行道王国》是在1999年发表的,直到现在,我还和这本书里的人们保持着联系。
邓奈尔特意住得离办公室很近,以便及时接送、照顾自己的儿子
发表《斯利姆的桌子》时,我还是个学生,书的销量极其有限。但在写《人行道王国》时,我已经是一个教授了。研究结束后,我和书贩们想到也许可以把版税收入分发给每一个人。所以《人行道王国》发表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和书贩们见面并分享版税。然而这些版税并不足以让他们变得富有。最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每个人能分到几百美元,但更多时候我要贴钱才能让每个人起码拿到一百美元。
尽管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不管这本书有多成功,版税都不会带来特别多的收入。但每当版税收入走下坡路时,总有书贩会质疑我是不是在“耍他们”。这也让我意识到,无论我怀揣着怎样的善意,我始终是在历史关系的意义上“拥有特权与优势的中产阶级白人”。我只能接受他们的质疑。
Q四开能够与研究对象分享版税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情,每人每年一百美元的版税收入足以说明这本书已经很成功了。
A米切尔·邓奈尔 的确,对于大多数民族志书籍来说,分享版税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民族志研究者必须不断问自己 :如何才能减轻研究对象“被剥削的感觉”?
这些人并没有希望或者要求我们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主动选择进入他们的生活时,就等于做出了一份道德上的承诺。我们不需要在余生中和他们成为挚友,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些努力。钱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回馈社区,其中之一就是表示尊重、善意,并保持联系。
邓奈尔在办公室工作时会让儿子在一旁写作业
Q四开这种要花一生来兑现的道德承诺,是否是将记者和民族志研究者区分开来的一点?
A米切尔·邓奈尔 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不过关于这两者的区别,我还有些别的想法。
首先是,民族志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你不能给自己定时间表,如果你按时间表完成工作,就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民族志学者。你必须愿意浪费大量时间干坐、闲逛。你必须愿意失败,你必须愿意接受“也许这个研究做不出什么东西”——虽然事实证明最后都会有所发现,但当时你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个发现是什么。
社会生活大多是平凡的,而新闻工作者往往倾向于关注某些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黛安·哈格曼是一位摄影记者,她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名叫《我如何学会不当一个摄影记者》。在书里她提到,当她被报社派去报道高中体育赛事时,编辑永远希望她带着一张“冲过终点线的人高举着双手”的照片回来。但她更感兴趣的其实是站在旁边的人,他们根本不看比赛,而是吃爆米花、买热狗、闲聊。然而如果她带回来的是这些人的照片,编辑往往会问:“你在干嘛?”
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给民族志学者带来很多思考。你的工作是展示生活,而生活绝不仅仅是穿过终点线的那个人。那些吃爆米花的人,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邓奈尔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白板和一张陈果仁的画像,他经常会和孩子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添加站长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echan.xtucq.com/naier/207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