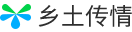一
一棵树站在大地上,伫立成一片风景。
600年前,洪洞大槐树下,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烙印在人们的记忆里,风吹不散,叶落有痕。祖先怀揣记忆远走异乡。眼看要像流水般翩然逝去,又总是在不经意的夜晚凸显出来,一树槐花与一豆跳动的灯花,比试着谁开放得更热烈。
世事变化,记忆中的大槐树,在隐藏,又在凸显,从不曾消失,连同树上的老鹳窝,是故乡留给每个迁徙人的最后风景,渐渐地,变成了抚慰心灵的思念图腾,穿越时空,顽强的成为基因的一部分,血液里流淌着故事,让一代又一代人记住它,并向它膜拜顶礼。
在洪洞,曾经的生活细节,像柔软的阳光,被浓郁的树叶筛得支离破碎,而生命中残缺的部分,却被身着明朝服装的现代人,以大槐树为背景,演绎着600年前柔肠寸断、骨肉分别情景剧。是错觉吗?几近真实地再版,让时间退回到几个世纪之前。我分明嗅到飞扬的黄土味道。
广济寺香火鼎盛。客人念念不忘的第一代大槐树,在清顺治八年汾河发大水时,被洪水冲毁,而由第一代大槐树根系孳生的第二代、由第二代根系孳生的第三代槐树,也历经数百年,饱经沧桑,郁郁的树冠,华盖般撑出阴凉。
根脉所系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表,在洪洞,我跌进了大槐树的浓荫里…作者:柳含烟,生命绵延,大自然轮回造化,暗合了东方人世代繁衍的观念,两者交相纠缠,让人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和源源不绝的生存。循着根系的脉络寻找祖先不停奔波的轨迹,以及远离乡土重新认识天下的过程。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传下去,说起老家自然会提起山西,提起大槐树,提起老鹳窝。
大槐树下,祖先当年出发的地方,黄土一年一年的覆盖,脚下的土地仍能传递出岁月深处苍凉的气息,他们的脚步或颤抖,或迟疑,离故乡越来越远,身如飘萍,向中原或更偏远的地方漫延,到陌生的地方安身立命。
洪洞古县,地处晋南,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汾河水终年喧腾,不知疲倦。广济寺院落宽展,可容数千人,寺旁汉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既是永久性的标志,也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禅院的宁静,在明洪武六年(1373年)随着第一批移民的到来被打破,到永乐十七年(1417年),50年间,移民18次,前后人数达100万人以上,881个姓氏,分布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18个省(市),500多个县。
古老的语言、习俗、手艺、饮食习惯,一次又一次地传播出去,在陌生的环境,与陌生的人群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世俗文化。
尘埃落定。祖先的原乡,让子孙们郁结浓浓的乡愁。
清明,在寻根的队伍中,我在槐树下孑孓而行,积郁在心头的的寂寞,云烟一样的飘散。
洪洞的山水与情怀,洪洞人的执著与热情,让我在大槐树下找到汇合点,彼此契合,彼此认同。
二
“是洪洞的景大启唤醒了人们的怀乡意识,”导游指着一座碑亭对我说:“自从他在这里立下这块碑,上书‘古大槐树处’,大槐树便成了人们永远解不开的一个心结。”
碑上的书法古朴、苍劲,透出儒家文化的气息。
景大启,洪洞贾村人,宦游山东时,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他们的祖先是从大槐树下迁来,而山西洪洞正是他的出生地。民国二年告老还乡,抑制不住内心对家乡的崇敬,与同乡刘子林联手募赀竖石,以志遗迹。
碑旁筑茶室数间,供寻根问祖者小憩、品啜,楣匾上书“饮水思源”,与碑坊雕刻的“誉延嘉树”、“荫庇群生”让寻根人抚今追昔,感念祖宗恩泽。根是树的魂,树死根不死,根死魂不散。香茗一盏,吸一口浓荫,树上的鹳鸟,不改苍凉的声音。
明初迁民,走的都是百姓子民,史官偏颇,记载寥寥,几笔带过。百万人的大迁徙不可能像秋天里的一片落叶,轻易飘落,不留声息。几段文字,如草蛇灰线,明里暗里,散落着蛛丝马迹,历史谜团。毕竟大槐树立在那里,族谱、家谱在坊间流传,口口相传的历史从没断线。景大启亲撰《古大槐树志》,刊印流布。黄土掩埋数百年的迁民足迹,重新显露出来。鼎沸的人声,官兵的呵斥,迁民的哭别,卷土重来,冲击人的耳鼓。
历史流动了起来,就像流动的汾河水,泛起层层白浪。
朱元璋一统中原,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又追到上都开平,再追到应昌,空空大漠,落日浑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已然无力回天,从里到外,元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
烽火连年,元军对农民军所在地“拔其地,屠其城”,使中原百姓十亡七八,莽莽中原,饿殍盈途,少有人烟,土地撂荒。
凭借地理的险要,晋人却独守唐魏遗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气定神闲,乐业安居。日明月朗,汾河水、霍泉水滋润沃野,庄稼一茬一茬种,粮食一茬一茬收。荷香满塘,银鱼乍现,一派江南风光。好山好水聚来人气,为避战乱,人们从各地迁居过来,悉心耕耘,繁衍生息,不问世外沧桑。
一家一户日日为安宁打算。大国一统,朱元璋何尝不想长治久安?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沃野,百般凋零,中原乏人,天平失衡,伤的是国家的命脉。他向众臣降旨:“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他效法汉武帝、曹操的屯田之法。将士兵组织起来展开军屯。移百姓子民于中原,开荒垦田,进行民屯。要移民,他眼睛盯上了山西这块富庶的地方,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之人,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向中原移民。
晨钟暮鼓,梵音低回的广济寺,唐贞观二年始建,数百年里,独享晋南宁静安谧。古汉槐,树冠相叠,枝柯交错,浓绿如云。五月花开,香飘数里。粗大的树干镂刻着岁月的皱纹。老鹳在枝叶间搭窝建窠,日落还巢,静听晚课诵经。
迁徙开始了。人们迢迢而来,在大槐树下聚集,再迢迢赶往陌生地方。一片叶落,有大地接着,而那个陌生的地方,是否能承接得住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土地,隔山隔川,隔断了老屋、家什,隔断了欢笑、喜悦和温情,也隔断了血脉亲情。背负“父母在,不远游”的名声,心揣“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千年古训远走他乡,迈出第一步,命运和未来陌生的地方紧紧地融为了一体。
走还是留?人到大槐树下没了半分退路。登记造册,领取凭照川资,编入遣送队伍,一一做下来。将领出发的命令一发出,整个队伍俄顷大乱。送行的人不顾一切地拥上来,和将要远行的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同行的弟兄,不能遣送到同一个地方,不经合计,把一口铁锅打碎,各执一角,日后持此相认,即便等不到那一天,一代一代传下去,子孙们会彼此相认。
包一包大槐树下的黄土,灌一罐汾河水,揣几片槐树叶,移走几棵槐树苗。一缕乡情,几分牵挂,眼睛看得到,手里摸得到,心里才踏实。老鹳每天都有归巢时,此番离乡,莫问归期。认命,走吧。
走吧,迈出一步,离故乡就远一尺。回眸再看,地平线上那棵大槐树和树上隐隐绰绰的老鹳窝成为最后的望乡。
繁琐的迁徙过程,也会让官兵头疼。为迎合百姓不愿迁徙的心理,他们到四乡贴出告示,佯称凡三日内到大槐树来登记注册的人,一律不迁,不到者随时听候。消息一出,百姓雀跃。故土难离,老天开恩,扶老携幼,有说有笑,三日内大槐树下聚了万余人。人声鼎沸,吵得老鹳都无法回巢。将领一声令下,兵士们从外围蜂拥过来,将人群死死围住。人们听到的指令竟是:凡来者,无论老幼,均在迁徙之列,即刻迁走,不得有误!
灾难降临的太快,还没等反应过来,心头的喜悦一冲而散。笑声变成哭声,声震四野。人被一一绑缚着,编组造册,分成各路,踏上了征程。人散后,广济寺重又恢复了平静。
槐树,一季花开,一季凋零。
人间故事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表,一场谢幕,一场上演。
旅途漫漫。心事重重的人逐一上路。
“报告,把手解开,我要方便。”一个人向士兵请求。士兵照做了,由他方便。朝夕相处,这句话简化成“解手”,队伍里不时传来“解手”的声音,听到喊声,士兵心领神会,一次次解开绳索。
特殊的语境,诞生了特殊的语言,普及开来,流传下去,600年的时间里,含义没变,今天的人们几乎天天重复着祖先创造的语言。
“如果你是迁民的后裔,凭着你身体的某些特征就能从这里找到祖先。”导游盯着我的双脚开玩笑地说:“俗话说‘谁是古树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当年,为了防止迁民中途逃跑,临行前,士兵会用刀在每人的小趾甲上割一刀,割成两瓣,做个记号,有这个记号,跑了也会被抓回来。这个标记,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就形成了复形。不信,脱鞋试试看?”
趾甲复形说流传很广,它是与心灵伤痛并存的肉体伤痛。这种伤痛潜伏在人们的身体里,形成基因密码,被一代又一代人复制下来,传递着遥远的信息,信息苏醒时,就会来到大槐树下纪念祖先。来不了,也会打发一个梦回去,守在树荫里,消解盘踞在心头的冗长的乡愁。
三
京剧《玉堂春》,“越思越想越伤情,洪洞县里没好人”,两句唱词,没有惹恼洪洞人,反而让洪洞县名扬四海。洪洞人永远有着侠义豪爽,慷慨大方,强悍耿直,幽默善良,同情弱者的性格。
我在大槐树下刻意流连,有意去寻找当地人身上的性格特征,并以我的家乡天津人作比较,悉心留意,两个地方的人竟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性格特征。
迁徙,奠定了天津这座城市。移民,给这座城市聚来人脉。“天津户籍最早者,大率由永乐迁来。”一座有根脉的城市,一座600年的城市,斗转星移,风雨沧桑,人们依然口口相传着大槐树、老鹳窝,还有燕王扫北。
“靖难之役”常被人们呼成“燕王扫北”。朱棣与侄子争夺皇位的战役,又一次重创中原。朱棣心中也有柔软的一面,渡御河南下一役,取得皇位,好的兆头正是从直沽的三岔河口开始的。念念不忘龙兴之地,念念不忘藏风聚气三岔口,取得皇位后,在这里设卫,钦赐“天津”。漕粮督运,移都北京,需要大批的人守住首都的门户。以三岔河口为原点,移民向四方散播开去。
吴歌柔软。江淮人乘舟顺水北上。
山西洪洞人,绕过山道,踏上土路。用双脚丈量着土地,黄尘随着行进弥漫开来。一路向东。
十几人的队伍,遇上几十人的队伍,彼此用乡音打着招呼,又各自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天黑之前,再走上几里,月亮爬上来,找个山坡或或干脆在路边宿营。鼾声打破空寂。星光灿烂,总会有人眨动双眼,在漆黑的夜里失眠。
没有人逃跑。一根长长的绳子,在出发时一一将人们绑在一起,青壮年双手背后捆住双臂,女人、小孩捆住一只胳膊,一字长蛇,走一起走,停一块停,露宿时也不会解开。
失去自由的迁徙,队伍走得很慢,毕竟奔赴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步一步的行走中,慢慢消解挥之不去的思乡之痛,慢慢地构想未来生活的蓝图,慢慢地思索是否还会有倦鸟知归的可能。
日日厮守,一根绳索无法把大家分开,命运也被绳索牢牢系在一起。在不远的将来,停止跋涉,一行人会永远聚在一起,聚成村落,一起耕耘,一同沟通,世世代代做好乡亲、好邻居。
陌生的土地,迎来陌生的主人。花开花谢,大地温存。
岁月中的海河,一头挽住大海,一头牵定大运河。与中原的其他地方相比,天津平原并不肥沃。西汉末年(公元前47年),一场大规模的海侵袭击了天津平原,海水吞噬了这片土地,多年后海水退去,沃壤不现,千年少有人烟。
绳索解了,脚落在地上,心还悬着。抬眼四顾,杂草丛生,野风呼号。从洪洞到这里1500里的路程,一步一步挪过来,无法再一步一步挪回去。
河流纵横,有鱼可捉;泥土斥卤,有盐可晒;野雁群飞,张网可捕,没有什么不能叫人活下来。断了回家的念想,几户人家聚成一个村落。有家才能安身立命,上风上水宜建宅舍。坐北朝南,抢阳通风,利出行,宜子孙。种一棵槐树,五月槐花开,弥漫着家乡的味道,寄托着怅惘的、无处安放的乡愁,这乡愁一路延续下去,在血液里蛰伏下来,等待一个契机,被子孙唤醒。
给村子起一个名字,用姓氏打头,或依环境入名,如初民的命名式中,有着祖先最初的那一种天真和好奇,洋溢着喜欢,然而又非常镇定,名字叫响了,就能永远延续下去。
挖去蒺藜,撅断芦根,焚烧野草,深翻土地,将生土晒成熟土,秧苗扎根,庄稼茁壮,秋天,老天会补偿人一年的辛苦。人与植物和谐相处,祖先与植物之间血脉相通,气息相通,空气似乎染成了绿色,人们呼吸均匀,眼睛明亮。物物有时,时时有序,每个时节有每个时节该做的事,草长莺飞,打渔狩猎,酿酒欢宴,都有其该沿寻的理路,有笃定,心中就会洋溢丰盛充实的喜悦。
一缕炊烟升空,家就在这儿,角角落落都散发着人间烟火的气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心中有情,脑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一日三餐,还是沿袭晋人的叫法:早晌饭,晌午饭,后晌饭。后辈沿袭了喜食面食、豆腐的习惯。独流老醋堪比山西陈醋的酸度。
踏出一条路,通往邻村或更远的地方,人做不到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给别人图方便,自己也留了方便,儿女亲家来回会多走上几趟,圆了一段好姻缘。
迁徙的脚步永远不会停下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子民,把故土难离的情结一次又一次地传递过来,一个村庄多了几户人家,多了几个姓氏,会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力量。
天地人和,依天时安排劳作,敬人,法天,遵循四季节令规律,简单生活,心灵踏实,一步一步顺着天地万物的秩序走下去。岁月绵延,生命代谢,儿孙的笑脸在眼眸中慢慢沉淀。
是人的力量,改变着自然,改变着生活,也改变着一代有一代人的命运。绵绵600年,海河水未断流,生命在延续,我们的血脉里保留住了祖先的全部的DNA。
600年,草绿了600回,槐花开过600回,祖先的大槐树情结还将传递下去: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老家名字叫什么,山西洪洞老鹳窝。
一座城市,一村一屯。从明永乐年开始,不管来的是江淮人,还是山西人,彼此把各自的乡音融合在一起,把生命中的血液融在了一起,用双手改变土地的命运,也改变一座城市的命运。子孙不离不弃,新移民又踏响新的足音。海河水养人。一方水土,一种精神。
移民的后辈,把祖先的异乡当成自己的故乡,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不停地创造着佳绩。
600年,矗立起的大都市。她是大地的奇迹,也是人的奇迹。
一座移民的城市,一座有根脉的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水一岸,无时不在发出锵锵的历史回音。
明初山西洞洪大槐树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群居性和舒适性的特点
群居性就不用多说了,那么舒适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儿女,有了自己的邻居,有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轻易是不愿意挪动的,因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得需要好长时间来适用。
那么什么情况下,人会进行迁移呢?
一个是发生大的灾害,这个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政府强制所谓明初山西洞洪大槐树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得不离开。
自然灾害很好理解,指得是发生大的火灾和大的旱灾水灾。
这些灾害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产不出粮食了,人没有的吃了,就只能到别的地方找食物吃,不去别的地方那我们就只能等死,没办法那就走吧。。。。。。
人为灾害是啥呢?就是战争!
这天天打仗的地方是不能待的,整天炮火连绵,我们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
天天提心吊胆,出去买个菜,“啪”,一发炮弹落在你身边,你不害怕那都是假的,
怎么办?只能走吧,离开这里。
那么政府所为呢?也很好理解。
就是执政者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牢固,会想方设法的增加对民众的控制。
比如钱多了,会想办法把你的钱在吐出来一些,
如果收入少了,想办法给你增加收入,如果吃不上饭的人太多,那不得闹事啊。
一个地方入口太少,得想办法用点优惠政策吸引人过去定居,
一个地方太穷,国家会给你补助政策,给你发点红包等等。
最终目的就是均衡发展,大众乐了,执政者也就放心了。
那我们在来看明初山西洞洪大槐树的移民就很好理解了。
自然因素:就是黄河泛滥成灾。
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45.8万户。
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
至正八年正月黄河决堤济宁路。
至正23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
至正26年2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70余里亦如之。
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大槐树移民,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有人要问,为什么皇上不管啊?
这个时候的皇帝是元顺帝,不是他不想管,是他实在是管不了了,自己东躲西藏的好不容易当了皇帝,这个时候各个阶层的矛盾很严重,官吏贪污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皇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哪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是如此。
有压迫就有反抗,农民就要暴动,那就打仗呗。
打仗就得死人,持续17年的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在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
战争使得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乐陵一县,仅剩 400 余户;潍县之族姓,惟存李、金二姓。
这就是当时作为主战场的实际状况。
而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哪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自然人口就众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最为皇帝的朱元璋就要发展生产了,先要把吃的问题解决,
中原地区土地是有的,但是没有劳动力耕作啊,不能土地闲在那里吧,
怎么办呢?只有迁移人口。
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
明朝大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当然有正当方式,也有连哄带骗的方式,这个肯定少不了。
那为什么叫做’洪洞大槐树“移民呢?
这就和洪洞的地理位置有关系了。
从政史资料记载从山西迁出的人口有很多地方,因为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派人管理此事,也是为了图个方便。
对咯,我得赶紧回家问问长辈们,自己的祖上是不是从山西迁移过来的,说不定哦!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添加站长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echan.xtucq.com/yimin/202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