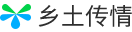摘要:孔子在判断华、“夷”时,主要以是否遵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的;孔子对华、“夷”的认识与当时的精英阶层的观念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固化了当时的华夏观念;孔子通过对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极力推崇和对华夏文化的宣传、维护,展示出强烈的华夏文化自信;孔子整理《诗》《书》《易》,编著《春秋》,规范、丰富礼乐文化,不仅身体力行,还将其广泛地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对礼乐文化的恢复与重建不遗余力。
关键词:孔子;华夷观;华夏自信;文化自信
先秦时期,以中原区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化观念特别是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关于“华夷”文化的认知无疑对华夏观的形成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孔子对华、“夷”的认识与当时的精英阶层的观念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固化了当时的华夏观,并且通过对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圣人的极力推崇和对华夏文化的宣传、维护,展示出其强烈的华夏文化自信。
一、孔子的“华夷观”
孔子在判断华、“夷”之区别时,主要以是否遵从周王朝的礼制文化为准则。凡是遵从周王朝礼制文化者为华,有违者则为“夷”、为“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其核心内容,其中“礼”作为礼法制度,上以治国,下以规定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它既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同时也是每一个循礼守法之人的行为外化,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所谓“克己复礼以为仁”也。终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而不懈地努力。因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王命不行,君臣之义不存,故作《春秋》,为的是让“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使“《雅》《颂》各得其所”[2]。相传他编辑《尚书》,也是为了“追迹三代之礼”[3]。
1.视尧、舜和夏、商、周为华夏一脉相承的正统
炎黄远而难追,颛顼、帝喾也很少被孔子论及,最受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孔子曾经如此评价尧、舜、禹三人,如尧:“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4]如舜:“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5]如禹:“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6]孔子认为,尧、舜、禹是人君的典范,他们不仅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也使文明礼仪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谓“焕乎其有文章”也。当功成名就之后,为天下寻找能够继任的新一代君主,且大公无私地将权力顺利地移交,以实现“禅让”,“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因为尧、舜、禹三代的经营,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
大禹之后,历经夏、商、周三代,虽朝代更迭,但其礼乐文化却并没有中断,一直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孔子一生都在从事“礼”的研究,不仅熟悉周礼,同时也了解夏礼与商礼,对于夏、商、周三代礼仪的沿革,《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夏、商之礼各有优劣,至周则兼两代之长而形成较为完备的礼法制度。所以当颜渊向孔子讨教治理邦国之术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8]孔子认为舜时代的《韶》舞是最完美的乐舞,后世无可替代;夏时的历法是最科学、适用的;商代的车子最简朴无华;周代的服饰制度能很好地体现出礼制。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说各个朝代的优秀文化只有夏历、商车、周冕,而是举其一端而已。足以说明,从尧、舜至夏、商、周,礼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代有损益,不断发展完善。
2.以是否用周礼作为判定标准
孔子根据鲁史而编定《春秋》一书,全书极力维护周王朝权威,批判讽刺君不君、臣不臣的违礼乱相,一字贬褒,微言大义。在《春秋》中,孔子对遵从周礼的诸侯多根据其封爵等级称之,如称为公、侯、伯等。但对不遵从周礼者多以“子”称之,如称楚君为“楚子”、黄国之君为“黄子”等。《春秋》中对杞国之君称谓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这一思想。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周灭商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9]。《春秋》《左传》等史书中称杞国之君一般为“杞公”“杞侯”或“杞伯”。但是,在《春秋》中,也偶然会称杞国之君为“子”,原因就是杞国弃周礼而用“夷礼”。如《春秋·僖公二十三年》载:“冬十有一月,杞子卒。”[10]此“杞子”就是《左传》中的“杞成公”,孔子为何不称“杞伯”或“杞公”,却以“子”称之,《左传》说:“书曰‘子’,杞,夷也。”[11]杜预进一步解释说:“成公始行夷礼,以终其身,故于卒贬之。”[12]可见,由于杞成公弃周礼而用“夷礼”来治理国家,在孔子眼中就变成了“夷人”。在此之后,杞桓公仍然延续杞成公的做法,用“夷礼”,《春秋》也用杞子称之,所以《春秋·僖公二十七年》曰:“杞子来朝。”[13]《左传》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14]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杞桓公再次到鲁国时,《春秋》直曰“杞伯”而不再称“杞子”,说明杞桓公已经舍弃了“夷礼”,复用周礼来治国,也使杞国不再被人以“夷狄”视之。
孔子的这种“华夷观”也代表着当时统治阶层大多数人的观念,反映出人们对日益崩坏的周朝礼制的焦虑。
二、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自信
从尧、舜、禹至春秋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流淌、积淀,经过周王朝的扬弃,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礼乐制度更加完善。但是春秋时期,出现了礼乐崩坏的局面,这使得华夏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孔子等人在为华夏文化自豪的同时,也充满了担忧与焦虑。
《论语·八佾》载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87在孔子看来,华夏与“夷狄”最大的区别在于礼乐制度,由于礼乐制度通过尧、舜以来至夏、商、周三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经过自上而下的推行,成为生活在华夏文化圈中的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虽然一时无君,而社会秩序井然;“夷狄”虽有君王,但因为无道、无礼,永远处于蛮荒时代的文明程度。孔子之言充分体现出他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与强烈的优越感。因此他极力致力于维护华夏文化,同时也极力推崇遵从华夏礼乐制度的政治家们。
孔子曾经评价过很多历史人物,而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们持肯定态度的并不多,管仲则是受孔子推崇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贡认为管仲应当称不上一个仁者,原因是管仲最早扶助公子纠,后来齐桓公杀死公子纠,而管仲不仅没有随公子纠而死,甚至接受齐桓公的封赏,成了他的国相。而《论语·宪问》载孔子语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丘博学院以前被留服认可嘛,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5]所谓“被发左衽”即披散着头发而不作发髻,穿着衣襟向左掩的衣服。这种装束是指古代中原地区以外少数民族的服饰习惯,即所谓“夷狄”之俗。孔子认为如果不是管仲,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作“夷狄”装束,丢失周礼了,管仲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那么,管仲做了什么能让孔子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呢?管仲坚持“尊王攘夷”。在管仲为齐相期间,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为诸侯霸主,但却一直奉行“尊王攘夷”的策略。齐国以诸侯之长的身份,却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承认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挟天子以伐不敬,维护周王室的权威与利益。他还打击那些不遵守周礼的国家,成为遵从周礼的诸侯国的依靠。如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齐国出兵救燕。
齐桓公二十五年,狄人攻打邢国而亡之,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16]。齐人派兵救邢,并帮助重建邢国。第二年,狄人又攻打卫国并占其都城,齐国率诸侯击退狄人,并帮助卫国在楚丘重建。齐桓公二十九年,楚国攻打郑国,齐桓公和管仲带领诸侯国联军救郑,并与楚人签订了召陵之盟,使楚人在较长时期没有大举北犯中原。周惠王去世,襄王继位,举行受赐典礼,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一带),在受赐典礼上,因齐桓公年迈而德高,特允许他可以不下拜,但管仲却说,周王虽然很谦让,但作为臣子的却不可不敬。最终齐桓公还是听从了管仲的建议,行了君臣之礼。齐桓公三十九年,叔带勾结戎人作乱,襄王外出避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正是因为管仲这一系列的政绩和对齐桓公的深刻影响,使齐桓公为诸侯霸主期间“讨东夷、伐西戎、战北狄、退荆蛮,尊周王、重周礼、一诸侯、平祸乱”,使得中原地区得以平安,周王室得以稳定,王权得以彰显。如果没有管仲和齐桓公,楚人可能早就灭亡了中原地区大部分国家,“戎、狄”也可能从西方和北方大举入主中原地区,周朝可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中原“沦陷”,华夏文化就会被“被发左衽”的“夷狄”文化所取代。尽管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的是霸道而非王道,管仲本人生活也不很节俭,偶尔也有僭越礼制的时候,孔子也曾批评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17],但是管仲对周王室地位的稳定和维护礼乐制度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虽然不能和成大器的圣人相比,但却称得上是当世仁人。
正是由于对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和出于对华夏文化的维护,孔子在为政期间,极为注重用周礼而攘“夷礼”,《史记·孔子世家》载齐鲁夹谷之会: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8]
在夹谷之会上,齐景公与鲁定公见面,齐人以主人的身份欢迎鲁定公,不奏周乐而奏“四方之乐”,孔子冒死进谏,逼迫齐景公改奏“宫中之乐”。为了助兴,齐人又让优倡、侏儒为戏,孔子认为这是俗乐、俗戏,不合周礼,要求罢去,齐人不得已而从之。因为这两件事,让齐人觉得惭愧,最终答应了鲁人的外交要求,返还以前所侵占的鲁国的郓、汶阳、龟阴土地,与鲁人和解。
三、孜孜不倦于华夏礼乐文化的重建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郑卫之音为时人所喜爱,雅乐地位受到挑战。孔子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唯有恢复业已被破坏了的周礼,使天下有所据,国有所法,民有所依,因而恢复和重建周礼就成了孔子一生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1.对礼乐的学习与传授
孔子在孩提时代,对于礼就有特别的偏爱与执着的追求。《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9]这种行为,既与他少儿时期家庭文化教育有一定关系,也与他一生的关注点相关联。
为了实现对礼乐内涵的深入了解和感悟,孔子一直广泛学习、深刻体验,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鲁国国君可以郊祀上帝、后稷,祭文王,并拥有周天子的礼乐。作为鲁人,孔子对鲁乐及周乐十分熟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周礼,相互印证,孔子曾赴洛阳,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相关知识,临告别时,老子对孔子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20]老子认为,对于形式上的礼仪制度,孔子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将其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告诫孔子不要随便议论别人,不要去深究别人的缺点。对父母、对君王不要太过于显示自我,在家要敬父母,在朝要维护君上。老子所讲的是“礼”的深层内涵,这些话对孔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21]“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22]“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3]这都是对老子语言的生动注释。同时,《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4]其中“毋我”也包含了老子所讲的“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之意。
为了学习礼乐,孔子到齐国,向齐太师学习,听到韶乐之后,更是潜心学习之,“三月不知肉味”[25]。说明在孔子心目中,什么美味佳肴,都不如音乐让人醉心,让人迷恋。孔子也曾经向师襄子学习鼓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丘博学院以前被留服认可嘛,王建旭 | 孔子的“华夷观”与华夏文化自信,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26]从这段话来看,孔子认为音乐学习有四个层次,即:习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习其曲”即学会曲谱,可以演奏;“得其数”即掌握演奏的方法与技巧;“得其志”即体悟其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得其为人”则是通过乐曲,领会创作者的思想精髓,感受其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由此,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孔子对音乐的深入理解和在音乐方面不同凡响的造诣。
对于礼乐的学习与传授伴随着孔子一生,《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27]即使在周游列国、身处困境的情况下,孔子也没有一天的懈怠,《孔子世家》载,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在无法进城的情况下,仍然和弟子们在大树下学习礼。孔子要求自己的儿子孔鲤学习《诗》,并对他说:“不学《诗》,无以言。”[28]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9]那么为什么《诗》会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这样的作用呢?《论语·阳货》中孔子的一段话给出了解释:“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0]孔子认为,《诗》可以启发人的心志与思维,可以观民风民情、政教之得失,可以实现情感交流,可以实现讽谏和批评。同时通过学习《诗》加强礼乐教育,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实现修身的目的,从而做一个优秀的儿子、称职的臣子。
2.对礼乐等经典的整理
其一是对《诗》的整理。今本《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既有庙堂祭祀之歌,又有文人士大夫之诗,还包括下层民间的作品,时间跨度长,地域广阔,作者众多,它并非成于一时,而是从西周到春秋逐次成书,最终在春秋中后期定型。《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31]、如果说孔子将三千首诗删除了十分之九而留其一,并且能让时人接受,恐怕不一定符合事实。但孔子整理过《诗》并将其作为教材向学生传授,这是肯定的。孔子自己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2]“各得其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诗》的文本,在孔子整理《诗》之前,可能会有雅诗混入颂诗,或颂诗编入雅诗的现象,孔子根据其内容,将其重新编入同一类诗歌,以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二是乐曲,“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可见孔子对《诗》中所有乐曲不仅十分熟悉,且都反复演奏过,尤其是雅颂之乐。在周代,什么乐曲在什么仪式上演奏本来都是有十分明确规定的,而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王道衰落以及诸侯、士大夫在礼法上的僭越,出现礼乐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有违礼的情况,如鲁国的季氏“八佾舞于庭”,而按周礼规定,天子之舞为八列,诸侯六列,大夫四列,士二列,每列的人数和列数都有具体规定,不得僭越。季氏以大夫用天子之礼,确实有违礼法制度。所以孔子痛心疾首地大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85正因如此,孔子很有可能按照周礼和个人对礼乐的理解,重新对礼仪乐曲进行了强化甚至调整,使之更加规范。
其二是对《尚书》的整理。《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33]孔子编定《尚书》,且向弟子们讲授,成为儒家弟子必读之教材。此《尚书》经秦代传至汉代,至汉却很少有人能习解之,汉文帝时求能习治《尚书》的学者,发现了伏生,文帝让晁错前往学习,世称之为今文《尚书》。
其三是对《易》的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34]说明孔子晚年痴迷于《易》,不仅反复学习、研究,同时还作了《彖》《系》《象》《说卦》《文言》等文章,以阐释《易》的起源及其哲学思想、卦辞和卦象的含义等。
其四是编订《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5]孔子据鲁史而订《春秋》,其目的是“使天下乱臣贼子惧”,但身处乱世,孔子不得直言,只好一字贬褒,微言大义。
孔子整理《诗》《书》《易》,编著《春秋》,规范、丰富礼乐文化,不仅身体力行,还以之广泛地传授于自己的弟子,对礼乐文化的恢复与重建不遗余力。孔子虽非王侯,但他却因为学问深厚而成为后世学习六艺者的宗师,成为“至圣”,虽王侯不可比之也。因此司马迁将之列为“世家”。
结语
孔子的华夏文化自信基于对从传说中尧、舜、禹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体制的充分认可,体现了他对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公旦等历代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无限景仰,也表现了孔子对从夏、商、周三代所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政治体系与礼乐文化的高度认同。孔子对华夏文化的维护和华夏礼乐文化的重建与传播,既体现出孔子对华夏文化深深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春秋以来礼乐崩坏的焦虑。孔子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也引起了春秋时代华夏文化精英的共鸣,并且成为先秦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作者王建旭为信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原文载《中州学刊》2022年第1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添加站长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echan.xtucq.com/qiubo/208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