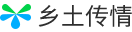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月26日晚,2023年度布克奖( Prize)在伦敦揭晓。时年46岁的爱尔兰作家保罗·林奇(Paul Lynch),凭借小说《先知之歌》( Song)斩获殊荣。林奇是继艾瑞丝·梅铎、罗迪·道伊尔、约翰·班维尔和安妮·恩莱特后第五位获得布克奖的爱尔兰作家。他的获奖作品《先知之歌》是一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讲述在近未来的极权主义都柏林发生的一个以良心反抗暴政的故事。
英国《卫报》评价道,“这部作品像是爱尔兰版本的《使女的故事》和《1984》,是一个你会遇到的噩梦般的故事:它强大、幽闭、恐怖,而且极为真实。”《观察家报》认为,“这是一本对当今时代至关重要的书,”因为它“呼应了巴勒斯坦、乌克兰、叙利亚的暴力事件,呼应了那些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
保罗·林奇(Paul Lynch)和他的小说《先知之歌》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访时,林奇表示,“他所有作品的共通之处2023爱尔兰移民,2023年布克奖与反乌托邦叙事下的爱尔兰寓言,是探讨当个人被困于巨大复杂的系统中,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寻求尊严和意义”。他的处女作《早晨的红色天空》描述了19世纪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林奇的灵感来源,是一部有关达菲铁路(Duffy’s Cut)的纪录片。这段由移民工人的血汗铺成的铁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以西,长约48公里。19世纪30年代,铁路承包商菲利普·达菲雇佣了57名爱尔兰移民来铺设这条铁路。但由于英裔与德裔美国人的歧视,这些移民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最终全部死于霍乱流行,他们的尸骨被丢弃在乱葬岗里,像一条条无人查看的索引。林奇擅长处理历史题材,他的第三部小说《格蕾丝》,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孩在那个动荡年代中的成长。
文学爱尔兰的诞生
除林奇外,入围本年度布克奖的爱尔兰作家,还有保罗·梅利、伊莱恩·费妮以及塞巴斯蒂安·巴里。林奇、费尼与梅利都是70后作家,正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也难怪柏林三一学院英文学院博士候选人奥莱丝·达琳得知这一结果后不无自豪地评论道,这届布克奖“标志着爱尔兰文学黄金一代的诞生”。那么,为什么爱尔兰文学能够在文学式微的当下异军突起?达琳认为,爱尔兰当代文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尔兰艺术局强有力的支持。僻如,自1969年起,爱尔兰政府就免除了艺术局的入息税,2022年10月,它们又正式开启了另一项经济实验,未来3年期内,艺术局将为2000多名创意工作者提供每周325欧元的最低工资。
不过,资金的投入只是表层原因,它创造了一个适宜文学生长的公共空间,但文学也必须有自己的根系,必须不断地打开它自身,与外部世界沟通2023爱尔兰移民,进行光合作用。爱尔兰文学的发展,似乎正应了布罗茨基对圣卢西亚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评价,当文明的中心崩塌时,原本的边缘地带反而会为文明保留它最后的火种。近代以来,爱尔兰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不亚于非裔美国人。即使只与大不列颠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英格兰也从未将爱尔兰视为本土。爱尔兰不过是距离英国本土最近的殖民地。
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晚疫症的爆发使得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出现粮食短缺,但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任何饥荒的产生都不应完全归咎于食品匮乏,造成饥荒的主因,往往是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时的爱尔兰由英格兰统治,岛上行政权归属于爱尔兰总督与爱尔兰布政司。由于殖民当局的不作为与英格兰辉格党的自由放任政策,粮食短缺最终酿成绵延十余年的大饥荒,期间,约100万人死亡,超过100万人被迫远走他乡,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 %,这一切促使爱尔兰人结成了一个受创的共同体,这便是近代爱尔兰文学的起点,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背景。我们所熟知的爱尔兰诗人W· B·叶芝,也正是在大饥荒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我们熟悉他那些颇具浪漫派遗风的早期诗作,却往往忽视叶芝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位置。他征引凯尔特神话,以这些神话为坐标系,重构他所使用的语言,而近代爱尔兰动荡的历史,进入他的诗篇,就像W·H·奥登在《诗悼叶芝》中所说,“疯狂的爱尔兰”将他“刺伤成诗。最终,英语在叶芝那一辈爱尔兰作家手中变型,这原先属于殖民者的语言,如今真正成为了爱尔兰的声音。
反乌托邦叙事
除了对爱尔兰历史的关注,在全球加速转向保守主义的当下,保罗·林奇等一众西方作家,仍然坚持以他们的书写,回应反乌托邦的阴暗图景。这样的书写几乎是一种警告。即使,从乔治·奥威尔的《1984》,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到玛丽·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所谓反乌托邦小说,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类型,而是已经有了自身完整的谱系。但这些小说中令人不安的预言仍会一再地刺激我们的想象力,虽然我们总会把它们化约为一种简单的寓言叙事,认定作者并非一个真正的政治学研究者,他所描绘的图景,至多是一出幼稚的政治惊悚剧。但我们仍然无法做到对这些简单的寓言视而不见。这或许是因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荒谬绝伦的,以系统为名的残酷也未必不可能发生。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的可能性,深嵌于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当中。故而,我们不能仅仅将这段历史交给纪念碑与博物馆保存,把它当成一个符号轻轻地绕过去。乌托邦是难以抵达的,但反乌托邦却有可能是现实的地狱。
《先知之歌》
在《先知之歌》中,爱尔兰遭受了与叙利亚同样的命运,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内战。爱尔兰人不得不向他们的祖先一样,离开故土,重新成为移民。林奇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写就这部小说,不分段的文字如同永无止境的潮汐,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强化《先知之歌》幽闭的氛围。他曾自述,这部小说的灵感源自叙利亚内战之后的难民危机。他注意到西方世界对难民的冷漠,难民涌入冲击着欧洲脆弱的人口结构,西方再一次意识到了那条将我们与他们,安全与危险划分开来的界限,人们从种族身份中辨认出这条界限。由此,曾经一度被压制的种族主义极右翼势力重新复活,并且一种捍卫欧洲文明的十字军叙事粉饰自身:他们的养分是普通布尔乔亚由于生存与就业空间被难民挤占而产生的不满,这些琐屑的不满加上意识形态的助燃剂,其结果就将是极权主义的再度出场。
这部小说,或者说所有的讲述未来的反乌托邦小说,它们所介怀的都是当下,因为当下就如同水滴一般,而我们的社会系统就像一块坚硬的岩石,当下之水滴,缓缓在岩石上蚀出未来的样貌,而反乌托邦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亚种,会呈现这为当下所蚀透的岩石的最终形态。经由此种描述,这些小说便切中了科幻真正的精神,科幻之价值,不止在于对未来科技的精彩预言,而在于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关心。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未经《晶报·深港书评》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作者 |谈炯程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添加站长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techan.xtucq.com/yimin/2050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