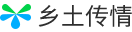简介:上世纪70年代末,22.4万越南华人被迫迁往中国,被安置在华侨农场,所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难民”群体,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人生?
越南归侨的深圳故事
“我们越南归侨……”
面对来访者,38岁的古秀萍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尽管她只在那个中南半岛国家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但这个特殊身份,在他的父母于恐慌中贱卖掉家产,带着8个儿女跨过中越边境时就注定了,并将伴随一生。
那是1978年,古秀萍6岁,中越交恶,一年后爆发了一场持续近10年的边境冲突。在此期间,约22.4万越南华人被迫迁往中国,形成20世纪后叶最大的难民潮之一。
古秀萍现在的家,在深圳市光明新区石介头村,这是个典型的越南归侨社区。它的前身是光明华侨农场的一部分——改制后的农场,至今生活着8000多名越南归侨和侨眷。不断崛起的工厂和外来人口彻底改变了它的原貌,也深刻地改变了归侨们和他们子女们的生活。
外观上,他们与当地人无异,语言和习俗的独特性也渐渐被稀释。现在,最能让外人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似乎与族群利益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有关。
利益诉求的根源是“土地”。
当初回国的22.4万归侨,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华侨农场,与原住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同,他们所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在征地浪潮日益凶猛、土地征收价格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这群“没有土地的人”,缺失了利益分配游戏中极为重要的筹码,在城市化浪潮迅猛的深圳,这种冲突格外典型。
这个命运,似乎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从祖辈耕种的土地上被驱赶的那一刻。3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小渔村深圳已经成为国际化都市,这个深嵌其中的“难民”群体,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迁徙
古秀萍第一次了解到家族与土地的命运,是从一种被客家人叫做“流水簿”的家谱上:清朝后期,他的家族在与当地人争夺土地的战斗中失败,从广西迁徙到越南靠近中国的边境上——那是一场被史学界称为“广西土客械斗”的历史大事件,数万人付出生命。
1978年,因为越南政府排华,古秀萍的家族再次遭到驱赶,从越南广宁省下基县向北跨过北仑河,进入中国境内。
那一年,两国即将开战的消息,已经在附近的村落里流传。
“听说越南政府要 把中国人都赶走,”19岁的严义章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太当真,当时他还是越南部队中的一名士兵,但是随着风声越来越紧,村子里迁走的人越来越多,他终于按捺不住,在一个凌晨逃离军营回家。
他清楚地记得,和妻子离开越南的那天是1979年农历九月初八。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从1977年到1989年,有22.4万华人跨过边界抵达中国境内。国内6省(自治区)的41个华侨农(林)场,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归宿。仅广东省就有23个华侨农场,土地总面积达107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万,其中的五分之一是归侨子女。
后来成为古秀萍丈夫的邓世光,也是祖居于下基县的华裔,1979年离开越南时,他6岁。
他的父亲把被褥、衣服、一桶油和一袋米挑在肩上,带着他和怀孕的母亲走了30多公里路抵达北仑河。对岸就是中国东兴镇,但当时河上的桥已被关闭,他的父亲游到对岸偷了一艘船才得以让一家人过河。
在东兴难民营的帐篷里等待了十多天后,邓世光一家人被大巴送往广东省光明华侨农场。1978年9月到1979年6月,834户、4300多名越南归侨,分6批抵达这里。
这个农场建于1958年,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接收因缅甸、印尼排华而归国的华人,并一度接收过上千名下放干部。
户口和身份证登记,也让归侨们很快得到了国民身份。与此同时,光明华侨农场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80万美金的救助,这笔资金被用于修建水库、学校和住房,“每个人能分到6平方米的砖瓦房,这种房子在当时算最好的。”光明侨联主席吴裕光回忆。
据广东省侨务部门公布的数据,1980年起联合国难民署就在中国开始了持续的援助项目,直至2003年停止时,仅广东省内越南归侨安置点就累计投入2100多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百万美元投入在归侨聚居地的校舍教学楼更新上。
这种以“土地安置”为基础的社会融合安置,有别于国际通行的难民营集中安置,效果明显。“在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等基础保障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工作时机。为帮助他们,当地的农民甚至自己住在暂时搭建的棚屋里,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住。”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办的一份资料如此表述。.
与广东一样,广西也是接收越南归侨的主要地区,两省、自治区一共接收了当初归国越侨超过一半的数量。
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人完全当作难民,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胞”和“侨胞”,所以当时负责该项工作的机构叫做“难侨办”而非“难民办”。
这一安置措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被称为“人道主义安置的典范”。
“不值钱”的土地
数量庞大的越南归侨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但在后来成为光明侨联主席的归侨吴裕光看来,这个变化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不适。
彼时这儿地广人稀,平均每个归侨劳动力要耕作8亩地。与农场相邻的原住民社区楼村,至今的户籍人口也不过3500名,但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约37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福田区。
但在当时,对那些荒凉贫瘠的土地,原住民和归侨们都没有多大兴趣。
吴裕光记得,1980年,农场将土地平均分配到个人,产出与工资直接挂钩,这个改革却遭到了普遍抵制。一方面,在越南过惯了集体公社生活的归侨们对这种新的体制感到恐惧,“认为农场不要他们了”,另一方面,则是“种这么多地实在太辛苦”。
这迫使农场领导宣布了一条“抛荒土地者将扣发补助”的规定。
充足的土地,有效抑制了冲突的几率。“土客”间良好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双方文化、民族上的渊源,“在越南的时候,我父母就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52岁的归侨严义明说,到来后,他发现当地习俗与在越南时的差别并不大,他很快适应了当地人的语言。
些许不同,来自于工作的性质。光明华侨农场的定位是副食品基地,喂养了大量奶牛。不止一位归侨抱怨,为牛场种收橡草,是一件远比种水稻辛苦的活,比人还高的橡草长满了绒毛,粘在皮肤上,刺痒难忍,“但终归是种地,和越南一样。”
当然这一认识,或许也存在一些宿命的成分,“我们是难民,有饭吃有地方住就很满足了。”
归侨农工们每月能从农场领取的工资,不超过30元,邓世光记得,1980年的春节,家里最奢侈的食品,是供奉在祖宗牌位前的一只鸡。
他们的原住民邻居们,尽管拥有更多的土地,但生活也没能好到哪去。后来成为楼村村长的陈东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学生的他经常光着脚,在稻茬地里踢足球,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双球鞋,“当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仅够吃穿,没有闲钱。”
几十年后,随着土地价格的暴涨,两个群体身份的差别遽然体现。
为城市化让路
1990年,17岁的邓世光小学毕业,从此辍学。读书的时候越南驱逐华侨,他最大的兴趣是每个周末上山挖药材、抓塘鱼,拿到就近的市场出售,可以获得几十块钱。当时他的父亲,每月从农场领取的工资只有150元。
邓的主要客户是富裕起来的当地农民。当地政府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当地农民于是将自家的山地开垦成荔枝林,获利颇丰。
但农场职工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2002年,租种了农场十几亩土地的邓世光夫妇,还必须在其中的6亩地上种橡草,作为供给农村奶牛的草料。
农场提供种子、肥料,并负责收购。在邓看来,种橡草是一件辛苦且无利可图的活儿,“但必须种,否则租不到地。”
彼时的农场仍是政企合一的体制,拥有自己的城管所、运管所、学校和医院。特殊的体制不仅导致农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且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少,极大制约了经济发展,”广东省农业厅一份报告指出。
广东省农业厅农村经济处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专题调研报告》中指出,全省华侨农场金融债务合计超过17亿元,其中光明华侨农场改制前的负债约2亿元。
这份报告中提到,政府将整合金融机构豁免这些债务中的80%。
与此同时,农场职工的生活水平也逐步与社会发展脱节。
2002年4月,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部分委员、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和省侨办联合组成调研组对全省华侨农场情况进行调研。调查报告中直白地描述了归侨们所处的困境,“近年来,我省侨场社会经济虽有新的起色,但与周边县镇相比,其发展速度仍较缓慢越南驱逐华侨,几十年积聚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全解决。这次调研的所见所闻,其困难和问题远比我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和严重得多,侨场职工生活水平普遍比不上当地周边群众。”
《粤港信息报》援引的一份2003年的报告显示:全省侨场人均住房面积13.5平方米,归侨人均11平方米,而归侨居住危房面积竟高达37.3万平方米,占归侨住房面积的40%。
从1985年到2007年,国务院多次颁发促进农村改制的文件。光明华侨农场于2001年改制为光明华侨农村(集团)公司,2007年光明新区成立,接管了农场改制后剥离出的土地、人口和企事业单位。
此时深圳市关内外的土地已开发殆尽,因体制拖累而发展缓慢的这片土地,成为深圳市最后一块“处女地”,承担了为深圳探索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铺路的重任。
这也意味着,50多年历史的华侨农场,要为此贡献出土地。
据光明侨联主席吴裕光回忆,他曾对一政府官员发感慨,归侨多年来开荒种地,对深圳农业做出贡献,如今土地却要被收回。这位官员的回答让他印象深刻,“没有土地,就没有光明新区”。
在农场工作了30年的吴裕光感叹“很现实。”
对邓世光和他的同伴们而言,这意味着农场不能再为他们提供庇护。
过去的十年里,邓世光做过流水线工人,摩的司机,倒卖过洗涤用品和蔬菜,但没有什么积蓄。2002年,他怀孕的妻子古秀萍还向当地政府打过报告,要求安排一份工作。
“土地财富”悲欢
同样是在这一年,楼村社区书记陈东华开始计划在村中建一个投资高达4000万的体育场,作为村民们的娱乐健身场所。这个梦想在2008年成为现实。
楼村是从城市化浪潮中受益的一个典型原住民社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楼村人发现出租厂房比卖荔枝更轻松更赚钱,于是逐步将村中的土地变为工业园。
与农场僵化的土地制度相比,原住民社区的土地使用性质变更要灵活很多。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现在,这个社区已经有超过600家工厂,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增加中,楼村社区官网透露:去年,这里增加了7家工厂,平均每家工厂每年要上缴40万租金。这些钱都属于村集体的收入,理论上,也是每个村民的收入。
对外人而言,楼村人每年获得的分红,仍是一个秘密。但这个社区的富裕显而易见,宽广的社区体育场和整齐统一的居民楼,与附近侨民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低矮平房,形成鲜明对照。
除了集体福利,楼村人还从拆迁中获利颇丰,在当地人的传说中,以百万计。
在几十公里外的福田区岗厦村,2009年的一次拆迁,则让当地出现了十多个亿万富翁家庭。这是土地致富的中国故事,所有人都明白,在城市化浪潮迅猛的当下,土地是最值钱的生产要素,谁掌控了土地,谁就掌握了藏宝箱的钥匙。
但光明农场的越南归侨们显然不是拥有土地的人。他们是身份特殊的“农工”: 是工人,但从事农业生产;是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每月从农场领取工资,耕种居住的土地为国家所有。
《归侨保护法》曾对这一问题做出规定,国家依法征收或征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地的土地的,依法给予补偿。但并未对补偿标准做出详细解释。
当时的法律制定者似乎并没有预见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这二者之间可能形成的巨大利益差距。
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年代,这些问题都被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掩盖。
十多年后,在类似于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剧,土地价值暴涨,当本地人从土地租赁和不断的拆迁中获益时,归侨们发现,“没有土地的”他们,缺少了最重要的博弈重码,随时都可能被挤下利益餐桌。
冲突
2003年时,古秀萍家租种的10多亩土地被征走一半建设同富裕工业园,没有获得补偿,又过了几天,剩下的土地都被征走了,“每亩只补偿了1800元青苗款。”
同样的故事还包括去年4月的广深港客专线沿线征地,归侨社区果林村一部分人的房屋被拆。政府最初给出的补偿标准是280元一平方米,后来提高到1000元一平方米,但绝大多数屋主都反对这个标准。
《南方都市报》记载了一场由此引发的冲突:2010年4月11日,上百名村民用燃烧瓶、石块对抗强拆者,坚持3小时后失败,2000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
报道此事的记者回忆,果林村所在的光明街道办一工作人员曾解释:所涉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非集体所有,“不是征地拆迁而是清场”,之所以给补偿,是出于人道主义。当地人则获得了不同的待遇。2004年,深圳市政府开始兴建公明水库,分别从楼村和归侨聚居的迳口社区征收走了一大片土地,当地政府没有公布确切的补偿数据(楼村按地的数量补偿,但迳口社区一名林姓归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楼村人却发了大财。”
抗争并非全无结果。古秀萍介绍,在有些归侨社区,一些归侨至今还承包有土地,去年的一次征地中,有人获得的补偿超过十万元一亩。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光明新区政府的证实。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光明农场的越南归侨和他们的子女,也从城市化的浪潮中获益。1995年,邓世光开摩的载客,昼伏夜出,平日里他最主要的客人是那些出入酒店的花枝招展的女人,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那些南下深圳的务工者,能给他带来每天五六百元的收入。那一年,他已经拥有了一部价值5000元的爱立信手机。
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几乎每隔半个月,摩托车就会因“非法营运”被执法人员扣留,或者车主被当成飞车抢劫者对待。邓的一个朋友,曾在一个晚上因拒绝停车被持枪巡逻的警察击中了轮胎。
也有人做生意致富,更多的人相继盖起了房子,把多余的房间出租给外来者获利。同时,光明农场退休职工的工资,也在全国农场中数一数二,每月超过3000元。
当地政府也曾试图给归侨社区引进工业。2010年,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宣布,在农场土地上建设的同富裕工业园,第一次为当地每个户籍居民“分红”1000元。当地政府希望,这个工业园能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并在一本纪念光明农场30年的画册中,将之宣称为“爱侨护侨”的典型。
同时,当地政府还在2003年实行了一项名为“强企富民”的工程,帮助归侨在原农场的土地上建设企业,并借给100万元的帮扶资金。先后有18家企业建立,由此造就了一批归侨企业家,但同时也引发了另一场与土地有关的冲突。
古秀萍所在的石介头村成立的一家企业叫江翔实业有限公司。她介绍,2004年,公司最初的发起人以400多个村民的名义向政府申请到了土地,但在工商登记资料上,股东则只有三个人。于是,一场“企业是私有还是集体所有”的争议,持续至今,并引发了多次上访。
去年的一天,上百个村民包围了江翔实业有限公司,并且往董事长黄廷光家的院子里扔满了牛粪。当地政府已介入调查,但黄廷光拒绝了记者采访。在光明,另外17家归侨企业,情况大致相似。
未来
归侨们的举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归侨社区凤凰居委会工作的一名本地女孩对记者抱怨,“这些人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做生意,一味等靠要,得不到就闹事。”
“不重视教育,是越南归侨的一大通病。”吴裕光感到忧虑。
直到2002年,光明农场的归侨中,才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
当地政府曾拨资上百万建设夜校,重点为归侨子女做再就业培训,“最后也没什么人去上课,好像都不大感兴趣。”古秀萍承认。
将近一半的归侨,都属于低保户,这个比例在深圳所有社区中是最高的。
年轻人也不愿意再种地,记者在归侨聚居的凤凰社区采访时发现,大量土地被出租给湛江、湖南等地的农民种植。他们更热衷于喝茶、赌博,“甚至有人结婚后,还靠着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古秀萍也对此感到忧虑。
这些问题在原住民社区也存在,陈东华投资4000万建一个社区体育场,就是为了给暴富之后终日赌博喝酒的村民们营造一个健康的休闲氛围。但这两个相邻共生30年的族群,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显然不一样。后者能从土地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前者则被迫逐渐远离土地,且所获甚少。
“有土地才能创造价值,没有土地,他们的生路就断了。”吴裕光认为,“政府要引导他们上路,这样才能和谐。突然让他们进入社会,压力大,阻力多,而且有很多不稳定因素。”
中青年一代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他们失去土地后的未来,吴裕光也感到担忧。
中老年一代归侨中的很多人,每年都会回越南祭祖,但这种遥远的跋涉,也越来越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传统和记忆正在逐渐消失。“这也算宝贝么?”4月初,归侨沈七妹家,她上初中的孙女指着老人从越南带回来的一个猪油罐哈哈大笑,90后一代更关注互联网、电影和明星,也很少再有人称他们“越南仔”、“越南妹”。
现实利益,似乎成了维系族群认同感的最牢固的绳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生博士孔结群对这一问题有如此论述,“现实利益是越南归侨维持难民共同体想象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反之,这种想象也是对现实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力较弱的越南归侨,日益边缘化。越南归侨维持对难民共同体的想象,折射出双重含义:一是这种想象提供了集体安全感,二是强调身份特殊性,是他们要求获取现实利益的策略,也是缩小与当地居民差距的愿望折射。”
当下,这个群体最核心的利益诉求与土地有关。在海南、广西、广东,失去土地的农场归侨与外界的不断碰撞,正逐渐演变成一场场冲突。2010年,古秀萍回了一次海南红华华侨农场。在这个她长大的地方,那些仍在耕作的人,所有的耕地人均已不足3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沿着她当初的轨迹,北上打工。
而在她现在居住的地方,按照2010年光明新区管委会的一份规划,10年后,这里将出现一座新城。8000多归侨侨眷,将离开现在居住的土地,进入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楼里。
这期间,又会演绎怎样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晓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添加站长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echan.xtucq.com/huaqiao/68703.html